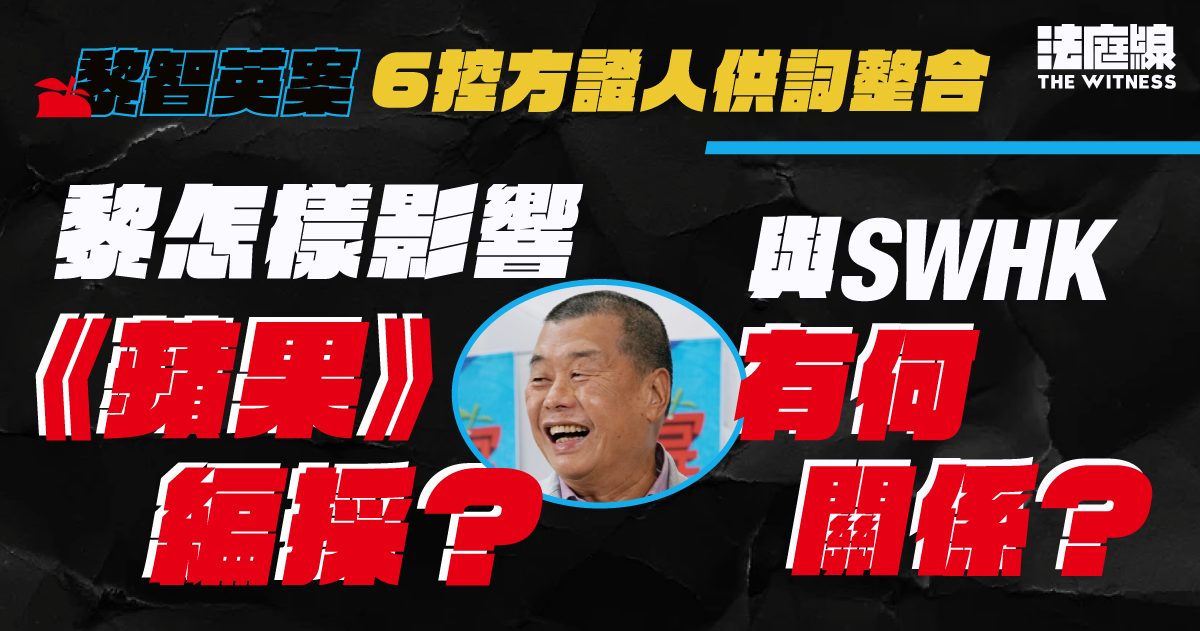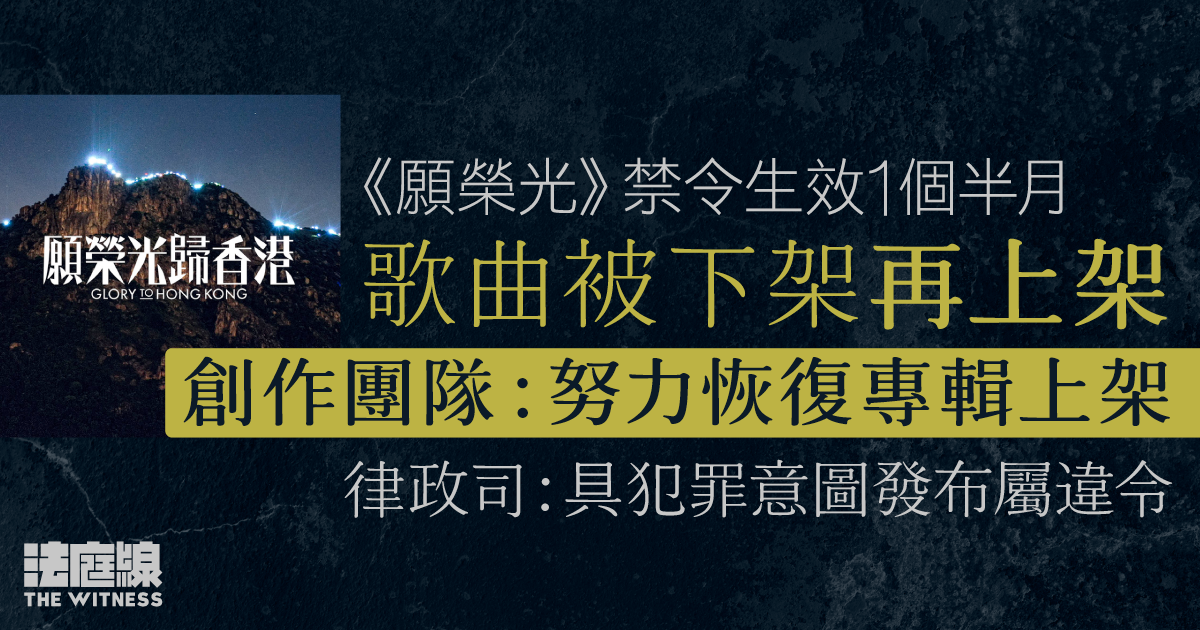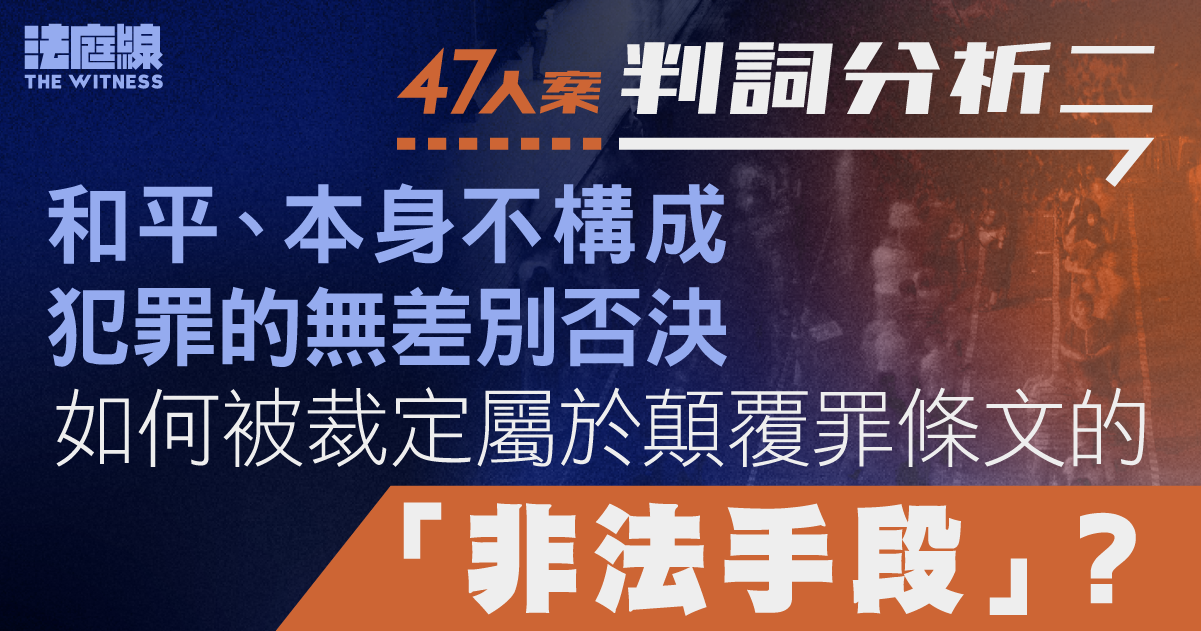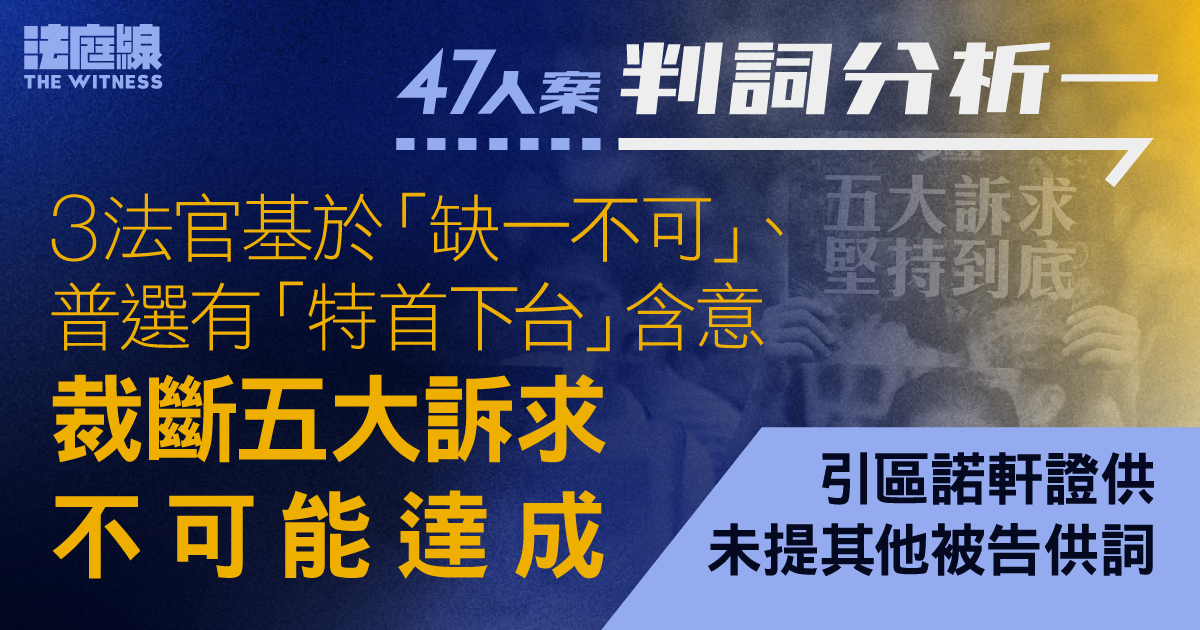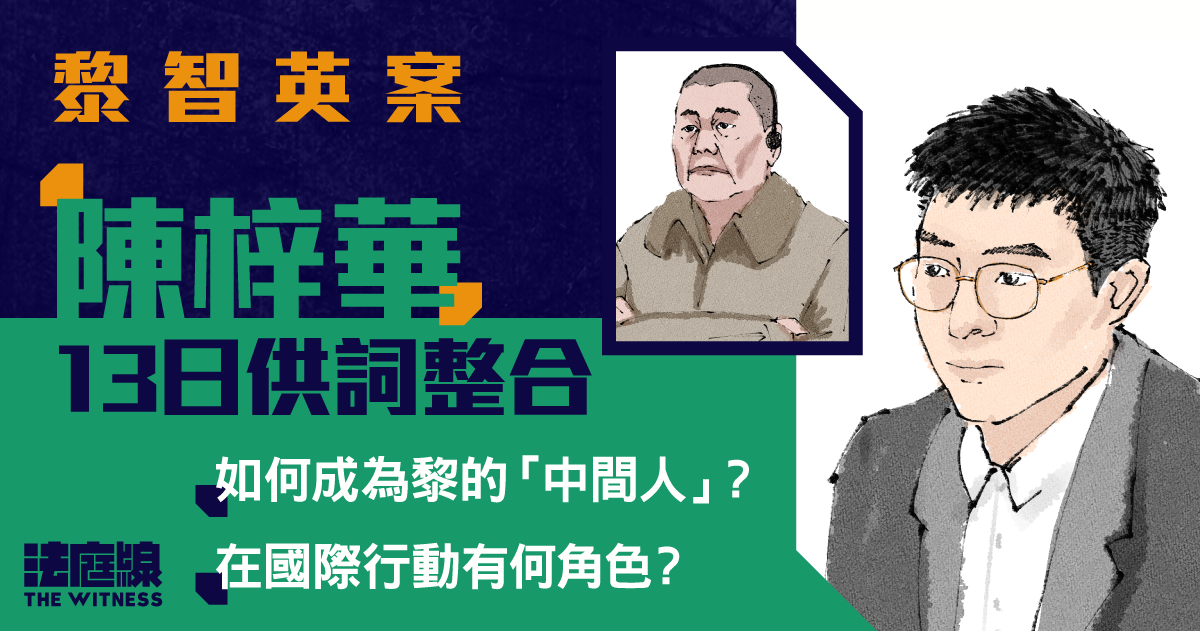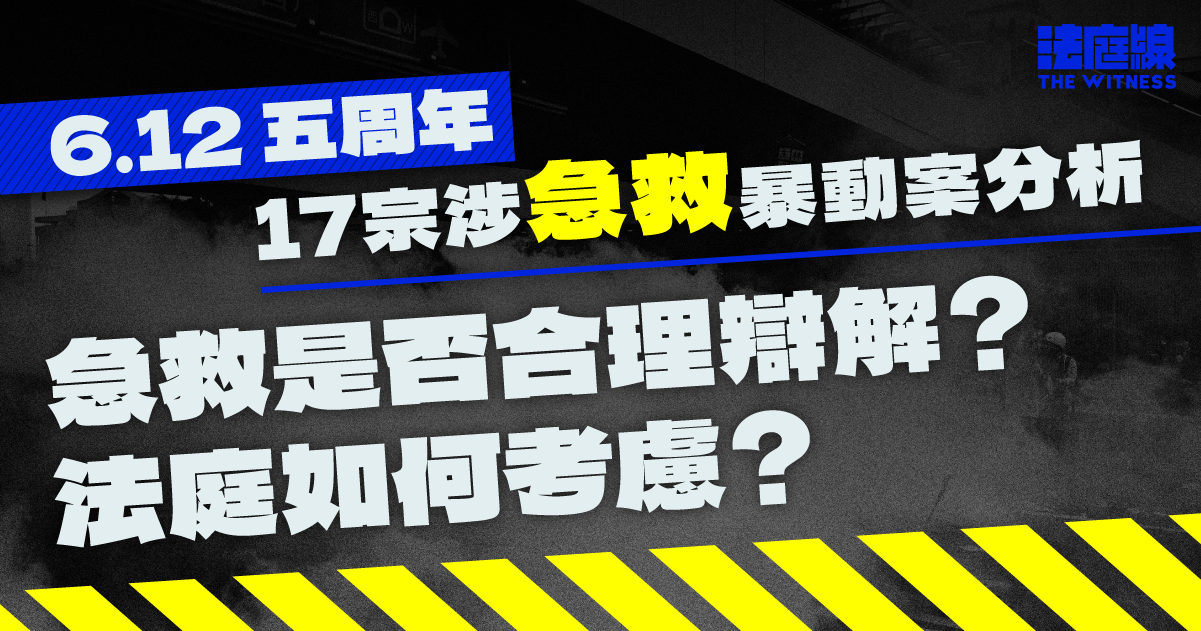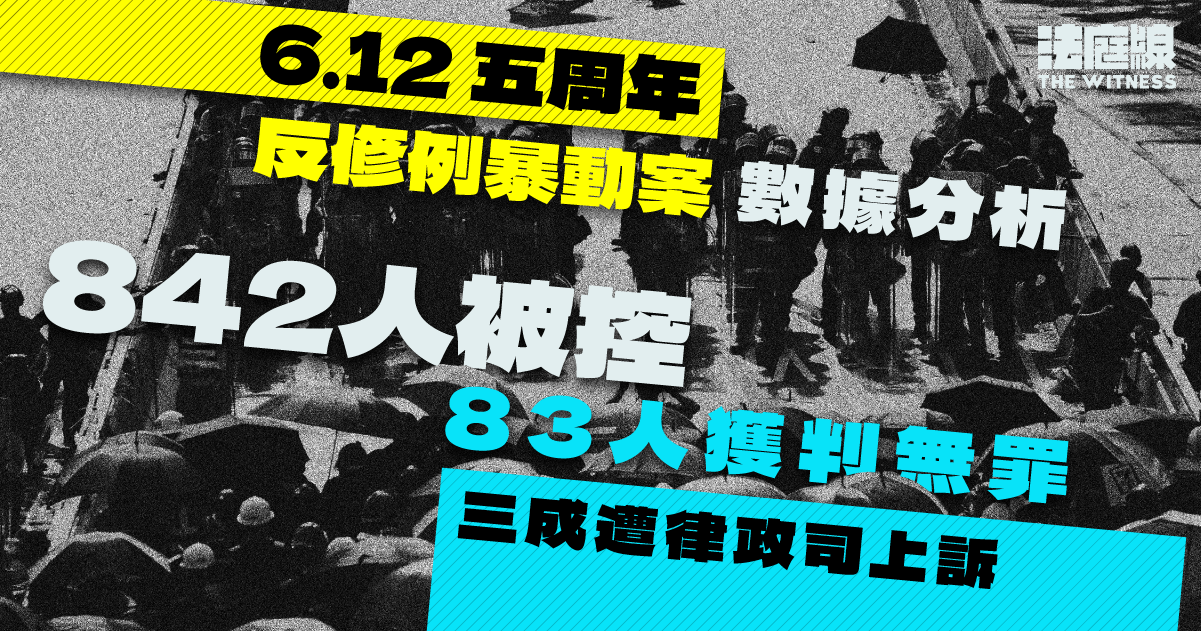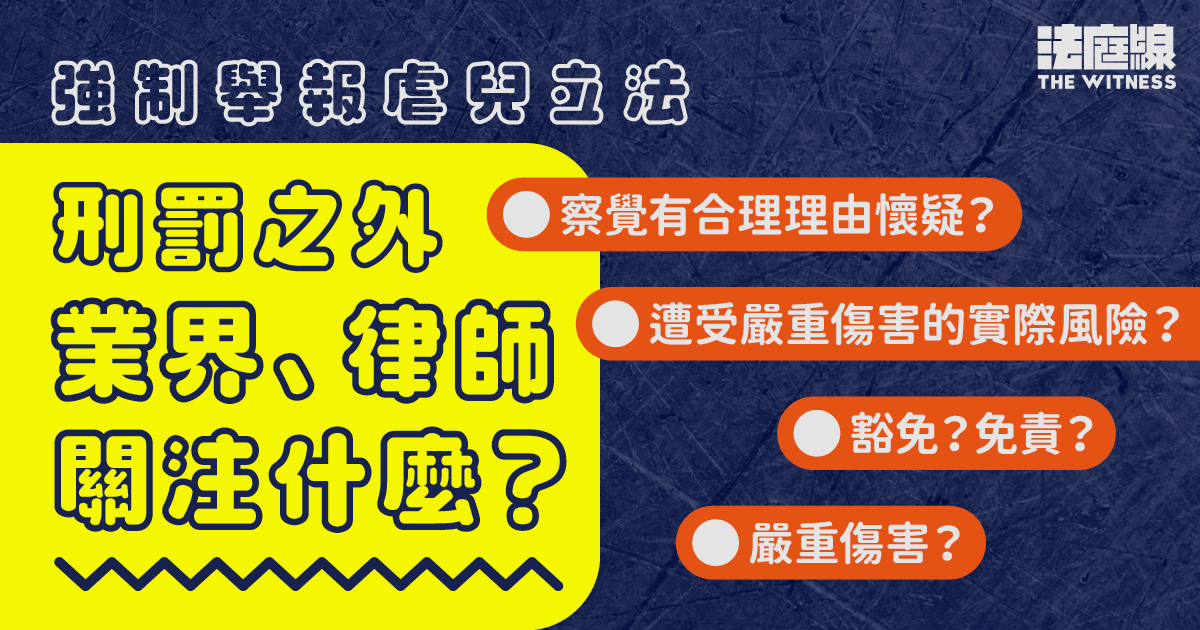黎智英國安案在 2023 年底開審,《蘋果》高層張劍虹、陳沛敏、SWHK(重光團隊)成員李宇軒等 6 人,先後以控方證人身分作供。控方於 2024 年 6 月完成舉證,控辯雙方將於 7 月 24 日作中段陳詞。《法庭線》整合證人供詞重點,回顧過去 90 日審訊。
黎智英被指是本案主腦,審訊重點之一是,他有否指示《蘋果》高層,透過報道推動國際壓力。高層均供稱,黎透過飯盒會及短訊,下達編採指示,例如要求將陳方安生與彭斯會面一事「做到最大效果」、以林榮基訪問催谷 4.28 大遊行。高層又指,《蘋果》基本上跟隨黎的看法行事,形容他「一錘定音」、「鳥籠自主」。
黎亦被指為 SWHK 提供財政支援,審訊另一重點落在黎與 SWHK 的關係。「中間人」陳梓華指,透過李柱銘向黎尋求墊支,曾將此事告知李宇軒。陳又稱,曾與黎見面 6 次,兩人曾討論「支爆」等事宜。李宇軒則指,他在行動後期才得知,黎名下公司有份墊支登報費,重申從未與黎見面及通訊。
各證人作供期間,亦有提及黎對「勇武派」、《國安法》等事情的看法。《蘋果》高層一概形容,黎主張「和勇不分」,藉《蘋果》報道表達對示威者的同情。陳梓華則指,黎曾批評「勇武派」濫用暴力,要求他著對方「克制」。
黎智英案審訊報道一覽
黎智英案時序專頁
身在現場 見證記錄